[内容提要] 共同犯罪是刑法中的一个复杂疑难问题,其危害远大于单独犯罪。我国现行刑法对共同犯罪中的某些规定也作了修改补充,这些规定对于司法实践中正确的处理共同犯罪案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我认为修改后的刑法关于共同犯罪仍然有可以进一步加以完善的地方,本文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现行刑法共同犯罪人的分类规定的完善及胁从犯的存废问题。
二、关于集团犯罪主体的人数构成问题。
三、关于主犯的处罚问题。
[关键词] 共同犯罪 主犯 从犯 胁从犯 教唆犯
共同犯罪是刑法中的一个复杂疑难问题,其危害远大于单独犯罪。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在我国还是西方,从古代的刑事立法开始就已经注意到了共同犯罪并在刑事立法中有所反映。例如在我国战国时期魏文侯相李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成文法典《法经》中规定:“越城,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曰城禁”。根据这一规定,十人以上越城,危害性大于一人越城,因此加重其刑罚。这是我国首次正式在立法中规定共同犯罪。其后,共同犯罪不断体现在后世立法中并日臻完善。及至《唐律疏议》,共同犯罪已经发发展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唐律疏议》对共同犯罪的规定分为总则性规范和分则性规范,前者是对共同犯罪的一般规定,后者是对个别罪名共同犯罪的规定,例如关于造意者在共同犯罪中负主要责任的规定,家人共同犯罪止坐尊长的规定,关于外人和监督主守的官吏共同犯罪的规定,等等,并为后世宋、元、明、清的刑律所照搬沿用。在西方到了中世纪也由开始有了关于共同犯罪的零星规定,而西方近代刑法中共同犯罪制度的确立是以1810年《法国刑法典》为标志的,该法典在刑法总则中确立了共同犯罪制度,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继之,1871年《德国刑法典》也对大陆法系共同犯罪制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现行刑法是1997 年3 月14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在1979年刑法基础上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次修改,对共同犯罪中的某些规定也作了修改补充,这些规定对于司法实践中正确的处理共同犯罪案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我认为修改后的刑法关于共同犯罪仍然有可以进一步加以完善的地方,以下分别叙述之。
一、关于现行刑法共同犯罪人的分类规定的完善及胁从犯的存废问题
(一)现行刑法分类规定的完善
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以便确定各个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条之规定,我国共同犯罪人被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这种分类方法兼采了分工分类法和作用分类法,其中主犯、从犯、胁从犯的分法是采用了作用分类法,而教唆犯的分法却采纳了分工分类法。以我个人之见,兼采两种分类法之长的分类思路是对的,但现行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却不尽如人意,仍有值得修改的空间,以下以古今中外已有的关于共同犯罪人分类的立法例是如何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作为引子,以得出我所认为正确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方法。
对共同犯罪中共同犯罪人如何进行分类,在历史上的刑事立法上曾有过三种分类方法:
(1)以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为标准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即分工分类法。
分工分类法始于1810年《法国刑法典》,该法典将共同犯罪人分为正犯与从犯两类,从犯还包括教唆犯与帮助犯,对从犯处以与 正犯相同之刑,这种分类过于简单化,更为关键的是其对正犯与从犯采取责任平均主义,这使得对共同犯罪人分类的意义大为逊色,因为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共同犯罪人公平的承担针对自己在共同犯罪中罪行的恰当责任,仅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而不区别其刑罚,没有任何意义。1871年的《德国刑法典》改进了这种分类方法,按照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将其分为三类:一是正犯,二是教唆犯,三是从犯,这种分类方法被称为三分法,这已经比《法国刑法典》的两分法有所进步;更值得一提的是,1871《德国刑法典》对共同犯罪人区别对待,对从犯采取得减主义,我认为这种区别对待才真正体现了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的原意,就确定各个共同犯罪人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责任。
分工分类法还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包括1919年《苏俄刑法指导原则》,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三类,即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还有1952年《阿尔巴尼亚刑法典》将共同犯罪人分为四类:即实行犯、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明确的增加了组织犯这一类,使分工分类法更为科学化、更为贴近社会实际,加大了对组织犯的打击力度。
(2)以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标准对共同犯罪人分类,即作用分类法。
中国古代刑事立法中对共同犯罪的分类是最典型的作用分类法,其最先为《唐律疏议》所确立。《唐律疏议》将共同犯罪人分为首犯和从犯,开作用分类法之先河,并为后世刑法所继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在刑事立法方面的成就。并且《唐律疏议》强调主犯犯意在共同犯罪中的危害作用,规定造意者为首,并从重处罚之,与我们现代刑法强调组织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两种分类方法各有其价值,按照分工分类法,共同犯罪人分为实行犯、组织犯、帮助犯、教唆犯,实行犯也称正犯,即自己直接实行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或利用他人作为工具实行犯罪行为(间接正犯)的共同犯罪,是实行故意和实行行为的主客观方面的统一,在刑法分则中有直接的规定,决定着共同犯罪的性质,可以直接定罪量刑;而组织犯、帮助犯、教唆犯则以实行犯的定罪为依托,在实行犯定罪的基础上再按照其刑事责任定罪量刑,其非实行行为由总则条文加以规定。因此这种分类方法有助于共同犯罪人的定罪,在量刑方面却有其固有的缺陷。而作用分类法却较好的解决了共同犯罪人量刑的问题,其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基本上解决了共同犯罪的量刑问题。这两种分类方法都有其历史发展渊源 ,西方各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从广义上被分为正犯(实行犯)和共犯,正犯直接规定在分则中,而总则规定共犯,由此可得出总则对共犯的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共犯的定罪问题;而我国古代刑事立法的总则对共同犯罪按作用分类是建立在刑法分则已经对共同犯罪进行了规定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国古代刑事立法中的共同犯罪全都是实行犯,已经解决了定罪的问题,因此可以直接在总则中按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行分类。而我国现行刑法似乎想兼两种分类法之所长,兼采两种分类方法,却没有注意到我国刑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当然刑法分则也将一部分共同犯罪中的组织犯、帮助犯、教唆犯直接予以规定,如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罪,煽动分裂国家罪),使定罪和量刑发生逻辑上的倒置,在司法实践中不利于司法机关正确的处理共同犯罪案件。[page]
我觉得按照定罪与量刑的逻辑顺序,还是应该先解决定罪问题,在解决量刑问题。因此,还是应当按照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分类方法,采用分工分类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先解决定罪问题;在对共同犯罪人定罪之后,再按照作用分类法解决量刑问题,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和从犯(胁从犯的问题后面会说到,我个人并不赞成规定胁从犯),这样定罪和量刑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完美的解决,也有利于司法实践。
(二)胁从犯的存废问题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是刑法中关于胁从犯的规定。在刑法中规定胁从犯是我国革命法制的传统,体现了我国的形势政策。关于胁从犯的规定最早出现在1945《苏皖边区惩治叛国犯罪(汉奸)暂行条例》中,该条例第三条规定:前条罪犯,得按其罪恶轻重,分别首要、胁从,予以处理。建国后,毛泽东提出“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明确指出:“胁从者不问”,这一政策在1979年被写入刑法,1997年修改刑法时仍然被保留,只是做了些微调,将“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改为“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去掉了“被诱骗”。从胁从犯的发展史来看,完全是我国政策法律化的体现,在我看来,胁从犯现在成为我国刑法中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干脆删掉。理由陈述如下:按照作用分类法,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可分为主犯和从犯主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对于主犯按照其涉及的共同犯罪进行处罚,按我国现行刑法,分为两类:①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全部罪行处罚。②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即这两种主犯都是按照其对共同犯罪应付的刑事责任进行处罚,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从犯,现行刑法规定“在共同犯罪中其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从而从犯也包括两种:①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②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对于从犯的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里规定的幅度较宽,不仅是“应当”,而且既可以从轻、减轻,还可以免除。我们现在比较一下胁从犯的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是胁从犯,对于胁从犯,“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对于胁从犯的刑事责任,完全被包含在从犯的刑事责任中。至于少了一项“从轻”,完全可以由法官去根据犯罪情节酌定把握。这还在其次,取消胁从犯的更充分的理由,可以从分析胁从犯罪的胁迫手段入手。胁迫手段可以从程度上分为三类:①重度胁迫,是指以杀害相威胁,这里的杀害对象既可以是被胁迫者本人,也可以是被胁迫者的亲属。在这种情况下,被胁迫者如果不参加犯罪,就会被立刻杀死,有时候,胁迫者甚至先杀死一个或几个人,以此来胁迫其他人犯罪②中度胁迫,是指以伤害相威胁,包括以重伤与轻伤相威胁③轻度胁迫,指以损害财产或揭发隐私相威胁。以上三类,我们又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第一种仅包括上面所说的重度胁迫,从其表现可以看出,这种胁迫很严重,被胁迫者完全是出于违心和无奈,如果不从,面临的就是自己或亲属的生命的消失,例如,抢劫犯抢劫银行,而银行工作人员及时打通了110报警,但在警察来到现场以前,歹徒用枪威逼工作人员用钥匙打开保险柜,这时已经有几名这位工作人员的同事因为不帮歹徒打开保险柜而被歹徒打死,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被胁迫的这个工作人员还谈得上意志自由吗?如果他不打开保险柜,立刻就会被打死,他这是只是歹徒用来打开保险柜的“钥匙”而已,已经成为歹徒的“作案工具”,没有任何意志自由,在这种意志因素缺失的情况下,被胁迫人根本就不具有主观恶性,如果被定行为犯罪,就违反了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应此不应被认为是犯罪(在英美刑法中,以死亡相威胁,构成威逼,而威逼是重要的辩护理由)。当然,在现实的生命危险消除以后,被胁从的人仍然帮助犯罪分子犯罪的,应当构成犯罪。
对于胁迫犯罪的后两种情况(中度胁迫,轻度胁迫),包括以伤害相威胁和以揭发隐私或损害财产相威胁等等非生命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被胁迫人虽说不是出于主观意愿,但他还尚有意志自由,因此具有一定的主观恶性,完全可以被归入从犯的范畴,由法官结合其在共同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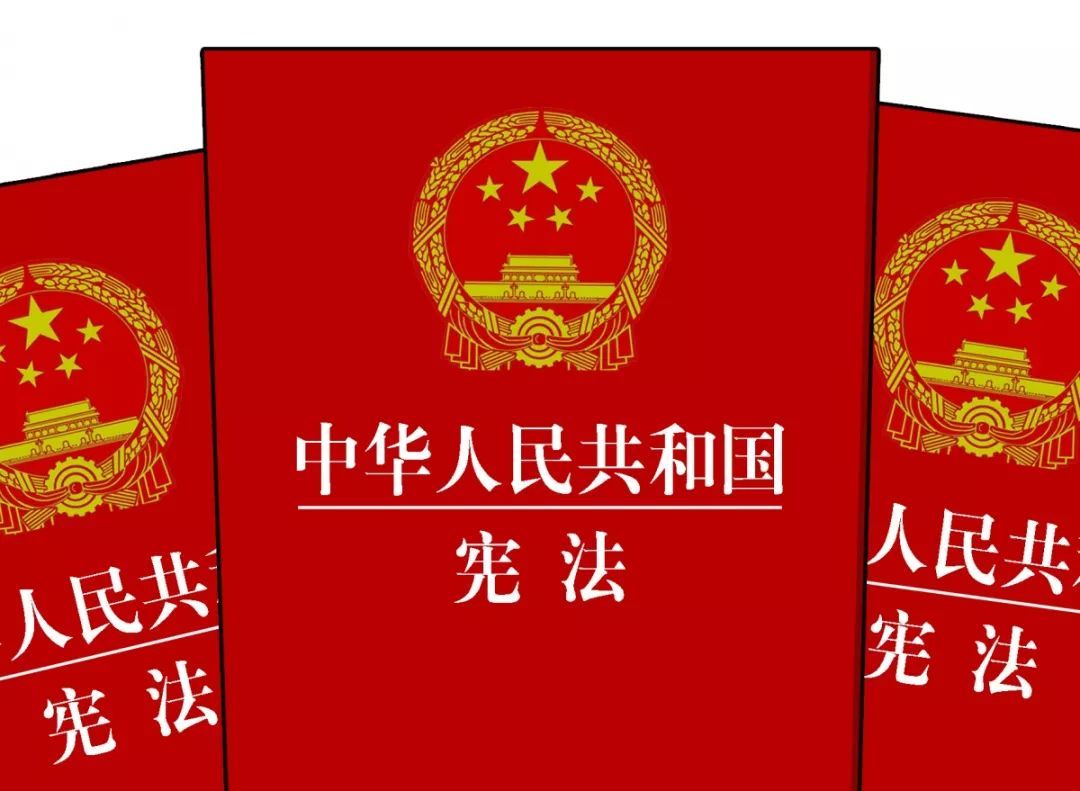 罪中的作用,决定对其的处罚。
罪中的作用,决定对其的处罚。
综上所述,现行刑法关于胁从犯的规定,可以被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重度胁迫,也即生命胁迫,被胁迫人没有任何意志自由,不具有主观恶性,不应被认为是犯罪;第二部分是中度胁迫和轻度胁迫,被胁迫人有一定的意志自由,因此具有主观恶性,被认为是犯罪,但完全可以归入从犯,由法官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参照法定情节进行处罚,而没有必要在刑法中规定这么一个政策性极强的胁从犯。
二、关于集团犯罪主体的人数构成问题。
集团犯罪是有组织的共同犯罪,它是一种最严重的共同犯罪,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在1979年刑法中没有关于犯罪集团的一般规定,1997年刑法增加了犯罪集团的概念,为正确认定集团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我认为现行刑法关于集团犯罪的构成人数规定为三人以上,并不妥帖,理由如下:
根据1997年《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在这里,立法对犯罪集团的人数做了限定,必须是“三人以上”,我认为对此限定过窄。其实关于犯罪集团的最低人数,在我国现行刑法修订以前刑法学界就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二人以上就可以构成犯罪集团,其理由是,集团二字与结伙同义,二人也能结伙,有伴即为伙,二人可成伙,因此犯罪集团二人以上即可成立,无需三人。并且按照我国和世界各国立法例,率以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为共犯,并非三人不可。①第二种观点认为,三人以上才能构成犯罪集团。其理由是,三人谓之群,有群才能有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之分。②陈兴良认为,犯罪集团只能有三人构成,他认为结伙和集团是有质的区别的,结伙犯罪是无组织的犯罪,而集团犯罪是有组织的犯罪。③我还是同意第一种观点,我并不否认结伙犯罪和集团犯罪的区别,但是陈兴良关于结伙犯罪和集团犯罪的质的区别的论述,并不能成为集团犯罪必须得有三人以上组成的合理理由,对于他所坚持的“犯罪集团必须有三人以上组成”没有说服力。第二种观点的理由也站不住脚,“三人谓之群,有群才能有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之分”,共同犯罪只能根据其具体实施的犯罪来划分,当然不是在任何一个共同犯罪中都非要同时具有以上分类,仅有主犯和从犯也可以构成共同犯罪。现在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很多案例是关于两人长期共同结伙犯罪的,性质非常恶劣,影响非常坏。并且两人团伙(集团)也很容易发展成更大的犯罪集团。放宽对集团犯罪人数的控制,将“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改为“两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可以加大对集团犯罪的打击力度,也更加符合社会发展实际。[page]
三、关于共同犯罪主犯的处罚问题
我国现行《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第四款规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这两条条款是在对1979年《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对于主犯,除本法分则已有规定的以外,应当从重处罚”修改的基础上制定的,而对该条款进行修订的原意是进一步加重对于主犯的处罚④,然而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适得其反。
按照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故意和共同犯罪行为的范围内,应对共同犯罪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经济犯罪要对犯罪总数额承担刑事责任(除贪污罪、受贿罪外)。例如新刑法实施以前有教科书指出:犯罪集团或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应对共同犯罪预谋实施的全部犯罪行为和后果负刑事责任,不管他是否直接参与实施某项犯罪。如果集团成员或者参与聚众犯罪者实施了预谋犯罪之外的犯罪,自然只能由实施该种犯罪的人自己负责。侵犯财产罪集团的的首要分子,应按照该集团侵犯财产的总价额处罚。⑤正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现行《刑法》所说的“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或者“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只是一种定罪原则而不是量刑情节,而且这种定罪原则是共同犯罪的应有之义,不言自明。
由上分析可知,现行《刑法》对主犯定罪的规定,没有实现立法者对共同犯罪中主犯从重处罚的初衷,进而导致对整个共同犯罪的量刑基点下降到与单独犯罪持平,从而无法体现出刑法对共同犯罪应比单个人犯罪打击为重的原则⑥,因此,我认为应该将现行《刑法》关于主犯的处罚规定改为:“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从重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从重处罚”,这样方能实现立法者的原意。
参考文献:
①参见吴文翰:《略谈共犯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研究》1982年第1期,第13页。
②参见辛明:《集团犯罪问题探讨》,载《西南政法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第38页。
③参见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第495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④参见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第534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⑤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页。
⑥参见蒋莺:《新、旧刑法关于主犯处罚原则之比较》,载《法学》1997年第6期,第45页